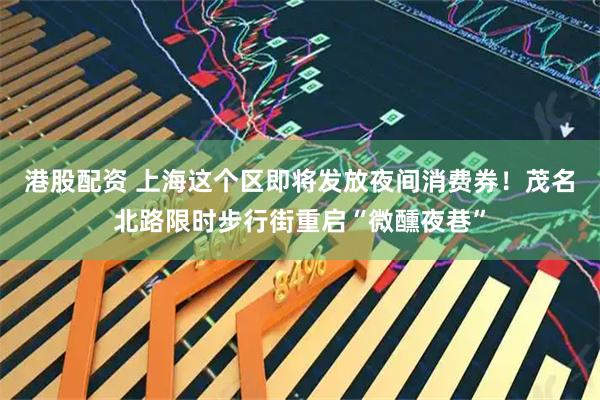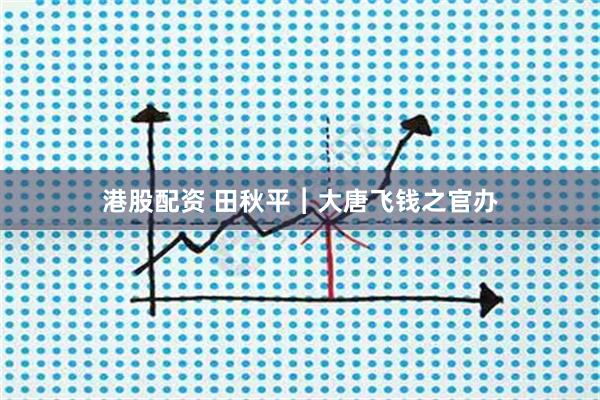
唐代贞宗年间,朝廷的三司分掌官办开始了飞钱使用。是唐朝经济历史上金融管控的初级探索与历史逻辑。
唐代,由户部、度支、盐铁三司主导的官办飞钱,是以卢旦、王播、王绍分域管理为核心模式,本质是中唐时期中央政府将民间自发的“汇兑信用”纳入官方财政体系的首次尝试。
这一阶段虽未形成全国统一的飞钱制度,但已突破“现钱运输”的传统桎梏,为跨区域财赋调度与商品流通搭建了初步金融桥梁,是中国古代官方金融从“实物管理”向“信用调控”过渡的关键起点。
一、三司分掌的底层逻辑:适配财政需求的“分工而非割裂”
卢旦(户部)、王播(度支)、王绍(盐铁)的职责划分,并非简单的“地域分割”,而是精准匹配了三司各自的核心财政职能,形成“发行-流通-回笼”的初步闭环:
户部(卢旦):锚定“民财汇兑”
展开剩余81%户部主掌户籍、租庸调,其管理的飞钱主要服务于民间跨区域贸易——如江南商人赴长安经商,无需携带巨额现钱,只需在户部属地机构存入铜钱,领取“飞钱文券”,再到长安户部对应机构兑付,既规避了现钱运输的盗抢风险,也缓解了民间“钱荒”下的货币流通压力。
度支(王播):聚焦“财政调度”
度支是唐代中央财政的“调度中枢”,负责统筹地方向中央缴纳的赋税(如两税)。其管理的飞钱核心作用是“简化赋税转运”:地方官府可将征收的现钱存入当地度支机构,凭飞钱文券到京城度支衙门核销,避免了长途运钱的损耗与延误,强化了中央对地方财赋的掌控力(尤其针对中唐藩镇割据下的财权流失问题)。
盐铁(王绍):绑定“专卖收益”
盐铁是唐代中后期最重要的专项税源(盐利占中央财政近半),盐铁司管理的飞钱直接服务于“盐铁专卖体系”:盐商从盐铁司购买盐引时,可通过飞钱汇兑支付货款;盐铁司在地方的盐场、铁冶收益,也可通过飞钱直接回笼至中央,形成“专卖-汇兑-财政”的垂直链路,确保核心税源不被地方截留。
这种分工模式的本质,是将飞钱与三司最核心的财政业务深度绑定,既降低了官方推广飞钱的“信用成本”(依托现有财政体系背书),也避免了单一部门主导可能导致的“信用滥用”,是中唐政府在财政压力下的务实选择。
二、“飞钱致远流通初级阶段”的核心特征:进步性与局限性并存
称其为“飞钱致远流通的初级阶段”,关键在于这一时期的官办飞钱已突破民间飞钱的“局部性”,但尚未实现“全国性”,呈现出鲜明的“过渡性”特征:
1. 进步性:从“私人信用”到“官方信用”的跨越。民间飞钱(如商人之间的“便换”)依赖的是个体商户或商帮的私人信用,流通范围仅限熟人圈层,且一旦商户破产,飞钱便成废纸。而三司官办飞钱以中央财政信用为背书,文券上会加盖三司专属印鉴(如户部印、度支印),兑付稳定性远高于民间;同时,三司在各州府的分支机构(如户部巡院、盐铁监)构成了初步的“汇兑网络”,使飞钱流通范围从“同城/邻州”扩展到“跨道跨区域”(如江南至长安、巴蜀至洛阳),真正实现了“致远流通”的雏形。
2. 局限性:“分域管理”导致的流通壁垒。初级阶段的核心短板,在于卢旦、王播、王绍各自负责的“管理范围”相对独立,缺乏统一的跨三司汇兑规则:
汇兑“不互通”:若商人在户部属地存入现钱,领取的户部飞钱文券,无法在度支或盐铁司的机构兑付,需重新在对应三司存入现钱,增加了跨业务场景的汇兑成本;
费率“不统一”:三司根据各自管理的业务类型制定汇兑费率(如度支针对赋税汇兑可能低费率,盐铁针对盐商汇兑可能高费率),导致同一地区、同一金额的飞钱,因所属三司不同而成本差异显著;
核验“不规范”:虽有印鉴背书,但三司对飞钱文券的真伪核验标准(如印鉴样式、文字格式)不统一,部分偏远地区的机构甚至无法识别其他三司的飞钱,导致“兑付难”问题偶有发生。
这些局限本质是“财政职能优先于金融职能”的结果——三司推行飞钱的核心目的是服务自身财政需求,而非构建统一的金融工具,因此“初级阶段”的定位恰是对其历史属性的精准概括。
三、历史价值:为古代官方金融体系埋下“信用种子”
尽管三司分掌的官办飞钱仍处初级阶段,但其对中国古代金融史的影响远超“汇兑工具”本身:
首次验证了“官方信用”在金融领域的可行性:通过三司背书,飞钱从“民间自发行为”升级为“官方财政工具”,证明了中央政府的信用足以支撑跨区域金融活动,为宋代“交子”(世界最早纸币)由民间向官方过渡提供了重要经验;
构建了“财政与金融结合”的早期范式:将飞钱与赋税、专卖等核心财政业务绑定,使金融工具直接服务于中央财权集中,这种“财政金融一体化”的思路,影响了后世近千年的官方金融制度(如宋代三司使掌财政与金融、明代宝钞与户部的关联);
缓解了中唐“钱荒”与“财权流失”的双重危机:一方面,飞钱减少了现钱的物理流通,间接缓解了唐代长期存在的铜钱短缺问题;另一方面,通过度支、盐铁司的飞钱调度,中央得以更高效地掌控地方财赋,在藩镇割据背景下巩固了财政根基。
总结
卢旦、王播、王绍分掌三司官办飞钱的阶段,是唐代金融从“民间无序”走向“官方有序”的关键过渡。它以“财政需求为导向”,虽因分工壁垒未能形成统一体系,却首次将“官方信用”注入跨区域汇兑,既解决了中唐的现实财政痛点,也为中国古代官方金融体系搭建了“信用框架”。这一“初级阶段”的探索,看似稚嫩,实则是古代金融从“实物时代”迈向“信用时代”的重要一步。
田秋平,中国作协会员港股配资,中国钱币学会纸币专业委员委员,中国金融作协副秘书长,中国收藏家协会古钱币专委。
发布于:山西省惠融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